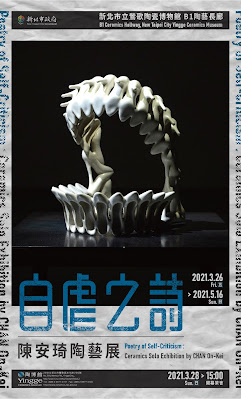文|
游原一
 |
| 2021,〈詠嘆調11〉,紙本、墨水、複合媒材、銀箔、鋁箔,35.5x37.5cm。(圖/黃至正提供) |
慨歎於物件,堆疊成回憶,在似近猶遠的物件裡,找尋自身存在的證明。物件,代表著生命曾經存在的現象,即便是日常生活習見之物件,經藝術家的凝視解讀後,物件也能在傳統及表面的意義之外,開展出某種隱而不顯的訊息符旨。「水銀落地」係藝術家黃至正(1988~)延續他對於過往事件與影像文本的興致,探索關於情感記憶與視覺經驗的實踐註釋。黃至正以遺世物件顯現生命中逝去的存有事實,視家族相簿和歷史照片所引起的記憶感悟為創作軸心,將視覺焦點聚焦於當下誘發情感的物件影像(如:家人形象、生活用品),且有感影像刺點的靈光乍現,仰賴可視覺化的縫線圖像、銀箔肌理、墨水變化及輸出影像等技巧,將蘊藏於物件內部不可見的情思意識引涉成可見的圖像意象,讓如碎片散逸般的記憶片段釋放出一連串的懷想氣息,令儲存於物件中的記憶意識得以再臨現場。意即,黃至正以外顯文本喚醒內隱情感的思考策略做為「水銀落地」創制之依據,試圖應用其主體知覺蒐集提取後的物件形象及檔案影像,勾勒其生命記憶中的情感狀態。
 |
| 2021,〈詠嘆調04〉,紙本、墨水、複合媒材、銀箔、鋁箔,68x98cm。(圖/黃至正提供) |
物件係經驗的本身,亦是記憶的碎片,物件需賦予意義才能變成具有寬廣精神價值的象徵事物,黃至正透過轉譯物件及場域的方式把自我感受投射於物件材料,使物件脫離自身的物質屬性又給予它原功能之外的抽象屬性,使物件肩負起自我意識和外界事物之間的情感交流任務。是以,因物感應所興起創作的「水銀落地」,仍保留藝術家慣於以往昔事件或影像文本作為構思礎石,將物件視為寄託情感媒介之創作特性,並承襲黃至正對於抒發個體內在情感的創作偏好,特別係著迷由物件所留存的紋理跡象所延伸出的消逝性(一種無法把握的逝去感),使其對物件產生歷史失落、生命消亡等外部情感的連結思維,以致他的創作總是染有某種無盡的緬懷感或是一種被遺忘的情感特徵。黃至正將物件形象和影像事件兩者疊壓為一種沒落華麗的視覺型態,在破碎變質的作品表面隱喻著時間、記憶、材質等概念,進而延伸借喻出物件背後的不確定性。「水銀落地」以物件輪廓(如:眼鏡)結合影像輸出(如:蕾絲)的表徵及意涵,使不可見的記憶移置眼前,除讓藝術家施以評斷個體記憶和自我存在間的反應外,本展有別以往銀箔作品的是,藝術家在詰問記憶的變動性與其形塑主客體之間的呼應過程,有意從再現個體性的記憶朝向擴充處理對時代集體記憶的共感創作。
 |
| 2016,〈侵蝕的記憶-家8〉,紙本、墨水、鋁箔、線,42X30cm。(圖/黃至正提供) |
更進一步就銀(鋁)箔系列的創作而言,無論係〈侵蝕的記憶〉(2016)、〈星象〉(2017)或是迄今的〈詠嘆調〉(2021),黃至正的創作語彙都指涉著主體記憶的歷史文本和時間軸線的消逝涵義,從而在一種超越知覺所能評斷的感知狀態中,尋覓主體的生命印記及過往物件相連的象徵痕跡。他常以今昔時空對照的敘事時間差,令自身的主體意識不斷往返於這些失佚物件所引起的迴盪聯想,將在這些物件影像中所察覺閃現的記憶情緒,融合著自身生命經驗的回饋,把它們縫合組裝成黯淡褪色的遺痕形象,經此表述著知覺意識曾經存在的情感。藝術家通過物件材料和背景影像之對應關係,讓作品展現一種遮蔽與顯現共存的美感效果,並借助這種冷質幽微的視覺映象,體現出那種失去現實利用價值的無奈感。故此,「水銀落地」係藝術家黃至正徘徊在對存有的取得與存有的失落之間所變造生成的視覺樣貌,他採取一種後設記憶的回望路徑,重探自身記憶與群體記憶二者相互滲透之情形。換言之,黃至正讓整個觀看記憶的過程,變得如同隔著帷幕注視一般,在奠基於真實世界卻又與真實世界遙望的視野中,喁喁細語著其個人面對物件時的獨白感觸。
 |
| 藝術家黃至正個照 |
 |
| 2021《水銀落地》個展文宣 |